编者按
动画无疑是属于全人类全年龄的,但它带给我们的最特殊的意义最特别的回忆却往往来自我们的童年。所以在儿童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真诚为大家献上一个崭新栏目“动画人事”。“人事”是一个有趣的词,可以指“人世间的事”、可以指“人情事理”、可以指“前途”、可以指“礼物”、可以指……总之,包含了各种我们在采访中感受到的或是想表达的东西。我们将在这里和许多动画人聊一些过往、当下或是未来的事给你听,每周五更新,长篇连载。
而我们的第一位分享者,他的动画生涯几乎都在为儿童服务,他是最适合在这个日子里给我们讲故事的人。他的作品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共同的童年回忆。这部作品带着他幻想的童心,科学的视角,对孩子们成长的关切,和对时代的责任感为他赢得了最广泛的声誉,却也成为他一个大大的遗憾。他就是黑猫警长之父——戴铁郎。

戴铁郎
中国著名动画片艺术家和一级导演,代表作《黑猫警长》。现任国际动画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理事以及中央电视台动画部艺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终身制待遇。
引子
耄耋童心,独居的乐观老人
已经88岁的戴铁郎老师长居杭州,只是偶尔回上海小住。那是一排解放初期建成的老式公房。红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在大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中,老公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去拜访著名的黑猫爷爷之前,我和他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到了某个弄堂拐角后,一直往前走,穿过一个楼梯再给他打电话。
我按照他的吩咐,走到了这栋老公房前给他打电话,刚接通,那头就传来老人家很兴奋的大声问候:“是XXX吗?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我急忙大声的回复:“是我,戴爷爷!”
两分钟后,我看到戴铁郎老师从三楼窗口探出头,他用力的呼喊我,问我在哪儿。由于眼疾,老人家需要通过声音确认我所在的方位,他好从三楼的窗口抛下钥匙给我。尽管早就在电话里听说戴老师眼睛不太好,但在当下我还是有点吃惊。
我拿到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的试,终于门开了,进楼,穿过油烟袅绕的公用厨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便见到须发皆白的戴铁郎老师站在门口等我。
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米的一居室里。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反而变得空荡荡的,沿墙靠着几块床板,唯一一张长沙发的两端堆放着不同季节的衣服。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老师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聊起晚年生活的他,依然充满乐观。只是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
我刚把戴老师扶到书桌边上坐好,他便热情的向我介绍起他身后堆积如山的画稿,“你看,我从来没停止过创作,我喜欢去了解那些新的科学知识,这样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继续为孩子们服务。你看,我的动画都是和科学有关的,我喜欢动画,喜欢和孩子们玩儿。”戴铁郎如是说。
第一章
红色童年,我和爸爸的秘密
1930年,戴铁郎老师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那时家里穷,没钱养活他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便把弟弟送给重庆的一个亲戚,年幼的戴铁郎老师就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散发写着“打倒侵略者”的宣传手册,一直到他回国。
回想自己人生的第一个20年,戴老师说:“我去过许多地方,但都是因为我的爸爸”。
1940年,因为叛徒出卖,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此时,上海地下党在之前的国民革命时期也被破坏的很厉害,需要一些没有露过面的党员来开展工作,于是,10岁的戴铁郎便跟着父亲踏上轮船作为掩护人员回到中国。

“怕引起注意,妈妈和妹妹不敢跟我和爸爸一块回国。所以只能先让妈妈和妹妹回上海,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从远地搬到上海。我和爸爸后去,住在龙华的一处草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一来就是这么多年,在上海各地躲来躲去。”
当时苏北盐城的情况很复杂,10岁的戴铁郎加入一个叫做新安旅行团的演出团体作为掩护,因为年龄小,个头小,所以演出的时候只能当指挥。
11岁就开始背着竹筒送情报,帮父亲做地下工作。14岁的他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有时还要去浦东背米,他说,“背两斗米就能养活妈妈和妹妹”,晚上则回家在灯下刻木刻画。
戴老的视力眇眇忽忽,讲这段话的时候,却手舞足蹈,话到深处依然热泪盈眶,或许,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提起爸妈,我们都永远只是个孩子。
“解放战争时期,我爸又被派往台湾、香港等地。时局紧迫时,全家人风声鹤唳,爸爸甚至不能出门。我以孩子的身份,曾经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

戴铁郎老师说,“我还单独回过上海,传递过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我那时带了许多中暑药,分散在袋装咖啡大小的包装袋里,情报其实就藏在里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爸爸从香港回到广州。我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香港《华商报》领了一笔路费,也回到了大陆。”
那时我想,“好日子要来了。”
“而母亲吃了半生的苦,也终于能够安定下来。”
第二章
贵在坚持,来自妈妈的教诲
“我和妈妈感情很好,妈妈很坚强,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妈妈是个大小姐,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除了养妈妈,还养了好几个弟弟妹妹,外祖母很重视学习,让他们多学习,正巧,那时候妈妈很喜欢艺术,就送她去学校学习,然后回家再教弟弟妹妹。”
“外祖父家也很有钱,妈妈来来去去都是乘坐老爷车。后来我外祖父要把妈妈许配给一个拥有两条马路的老板,做第二个老婆,我妈妈不喜欢那个老板,喜欢我爸爸。我爸爸本来家里也是有钱人,家里做锡矿生意,生意还很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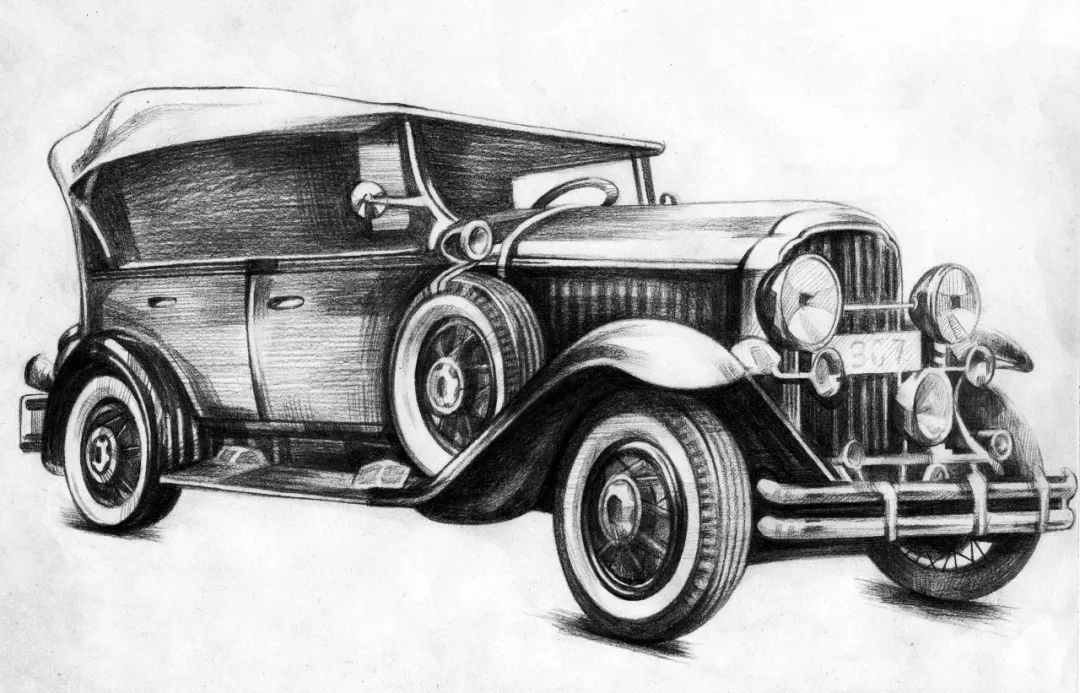
“我不是一个迷信之人,但有时候真的很奇妙,爸爸家本来养了一条狗,白色的很漂亮,那时还没有卡车,只能用大象来托运木材和锡矿,所以,狗狗就跟着大象后面,和主人们一起经营锡矿,生意很顺心。”
“后来,不知怎的,狗狗突然就死了,很奇怪,本来经营的好好的锡矿,在狗死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客户再来看锡矿,闪闪发亮的锡矿一下子就变成了土,黑黢黢的不发亮了。”
“到目前为止,我从科学方面还没有找到任何解释,也许这只是凑巧,也许狗狗的死和锡矿的变质根本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件事到后来我爱人去世,我觉得又未必没有联系。”
“我爱人90年代生病,糖尿病,为了让她解闷,我在南京路的花鸟市场买了只鹦鹉,天天陪她。”
“那时我爱人刚生病不久,我每天上班,所以鹦鹉陪她解闷,她照顾鹦鹉,互为伴,久而久之,感情很深。”
“我经常会去乡下去收粮食,比如玉米,我会带些回来给鹦鹉吃。”
“平时我出门会把窗户打开,鹦鹉很听话,不会飞走。但就在我爱人去世的那天,出门前窗户照常打开,我还用链条把鹦鹉锁了锁。”

“下午我和儿子去医院给我爱人送吃的,我让儿子先去医院陪妈妈说会儿话,我回家看保姆把饭烧好了没,然后带饭过去。”
“我回家,一进家门,就发现链条被啄开了,鹦鹉飞走了,看链条的样子,大概是鹦鹉的嘴硬挤进去把两个链条给挤破了。”
“我下楼去附近的几个楼找了一遍,无果。我想,她这么可爱,一定会有人可怜她,收养她吧。”
“随后我带着饭去医院,我的孩子就告诉我说,爸爸:‘妈妈一直在说小鸟飞、小鸟飞’。”
“我当时还想是不是我爱人又在搞什么创作?一定是工作上的创作,不然说不通,人在生病,但头脑还可以继续工作,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事实证明我错了。
“没一会儿,我爱人就走了。”
鹦鹉是人工饲养,飞出去肯定经不起外面的风吹雨打,会没命的。
“后来我想,鹦鹉飞走,可能是想念我爱人。”
“我总觉得宇宙间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弄清楚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但是还是没有想通。”
戴老轻舒了一口气,停了停,似乎又在想那些想不通的事。
“总之即便家道中落,妈妈后来还是跟爸爸走到了一起。”
“解放后,父亲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师从我妈妈。抗战期间,爸爸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妈妈一直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从无怨言,全心抚养我和妹妹,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
妈妈告诉我:“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对的,那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妈妈那个时代能这么做我非常佩服她,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88岁的黑猫爷爷老师,一口一声妈妈,听的心里真的好温暖。我想,在日后是非难辨的年代,或许是妈妈昔日的教导,使他得以摆脱愤懑,度过那些困苦的时光。
下期预告
第三章:青春正好,我的北京电影学院
我独自坐火车去北京考试。那年初冬,我只记得很冷,出门前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在车上越坐越冷。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第四章:芳华正茂,我来了上海美影厂
毕业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很巧,碰到了他之前在香港同画会(人间画会)的老朋友盛特伟,他当时是刚刚成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盛特伟就叫他去上海美影厂帮帮忙,当时戴老师就想,咦,不错啊。
于是他终究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直接赴上海美影厂报到。
他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的”。
(为了辅助大家更了解戴铁郎老师,L姐在公众号第二栏给大家准备了六一小礼物,人物小传 | 戴铁郎成就篇,请注意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