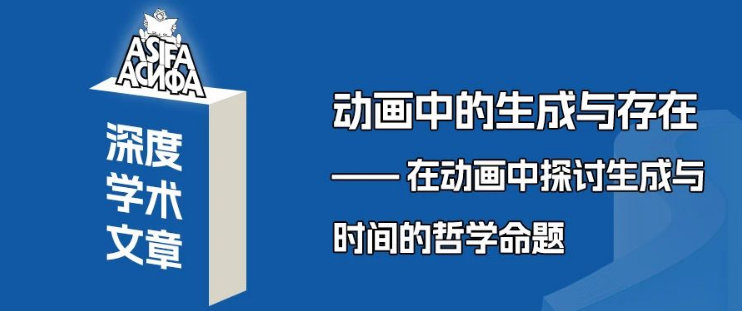
作者:Michelle M. Brand
文章基于哲学与电影理论的核心概念,聚焦亨利·柏格森的时间与生成理论,讨论“生成与存在”(Becoming and Being)这一对在哲学史中经典的二元对立问题,在动画中直指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一切处于永恒流动、变化与矛盾中”(becoming),还是“永恒不变,不可分割,变化只是感官幻想”(being)的问题。
首先,笔者将探讨动画如何通过“瞬间”实现“生成”,会以诺曼·麦克拉伦的动画Blinkity Blank (《线与色》)为分析对象,同时援引哲学家黑格尔与德里达的相关理论;
其次,笔者将通过动画的物质载体分析“生成”现象,会以雷恩·莱的动画Particles in Space(《太空中的粒子》) 、保罗·布什的While Darwin Sleeps(《当达尔文沉睡时》及尼基塔·迪亚库尔的Ugly(《丑陋》)为分析对象。
最后,笔者将以运动本身的“在场性”为切入点,分析索尔维格·冯·克莱斯特的动画Panta Rhei-Tout s’ecoule(《万物流变》)和平冈正展的动画L’oeil du Cyclone(《在暴风眼中》), 并通过这些案例重点阐释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体系——该理论是构成黑格尔与柏格森思想的重要基石。
基于相关哲学理论和动画案例,我将从四个维度总结动画与“生成”的关联:瞬间性生成;物质载体生成、银幕效应生成,以及本体性生成。
2. 动画作为探讨“生成”的哲学平台
作为个体,我们始终处于多维度的持续发展之中,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变化的发生。变化会催生差异,而正是通过当下状态与过往状态之间的差异,我们得以觉察变化的存在。这种认知逻辑意味着:我永远无法完全等同于“当下的我”,却也永远不会成为“非我”(“非我”指与“当下的我”完全异质的、断裂的存在状态)——我始终处于“成为自我”的生成过程之中,永远栖居于过去与现在状态的差异地带。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时间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成的过程,而我们始终处于这个持续的流变之中。这导致了一种对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如果当下的“我”正在不断变成另一个“我”,那么我们究竟是谁?
这种哲学思考与动画有何关联?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De Anima)中指出,变化必须通过运动来理解。如果宇宙遵循变化与可变性的法则,那么运动就是理解这一法则的关键。亚里士多德甚至将运动视为生命的原则,并将其作为判断某物是否具有生命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运动和变化都需要通过差异才能实现。
动画艺术正是基于这种内在关联而运作——通过每一帧画面产生的差异展现变化,从而呈现出运动。因此,动画的内容向我们揭示:事物必须经历持续的变化与运动,才能获得生命与存在。
电影艺术已经提出了关乎我们自身与媒介本质的存在论命题,而动画将这种追问推向更深处。笔者认为,动画制作以其独特的运动生成机制,不仅让我们得以探讨被呈现之物的存在本质,更促使我们反思见证这些存在诞生的观众自身的存在状态。
要探讨动画中的“生成”现象,首先需要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生成概念——即我们如何在与自我及时间的关联中感知这种持续流变的过程。
3. 亨利·柏格森的时间和生成理论
亨利·柏格森深入分析了变化现象、根源以及我们如何体验这种与时间流逝相关的过程。伯格森指出:首先,作为人类,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比如经历不同的情感状态。但我们往往假定某一状态会持续存在,直到被下一状态取代。然而现实中,万物皆处于持续变化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两点:其一,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持续变化中;其二,作为生命体,我们自身也在持续变化。最终可以断言:运动的连续性构成了万物存在论的基础。
但关键在于:当我们身处这种变化之中时,如何才能感知到自身及周遭的变化?
3.1 思维的电影化机制
柏格森提出,人类感知的根本功能在于再现周遭事物,但认知本身却无力把握持续运动中的存在。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会主动寻找参照点,将其固化为一系列离散的静态图像,用以表征变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
这就意味着我们以间断性的表征替代了连续的现实。我们将“生成”理解为固定节点,通过状态的差异来辨识变化,而非真正观察到生成过程本身——从而将注意力从真实的运动中转移开来。
柏格森指出,这种“通过静止来感知运动”的惯性认知方式,使得“我们普通认知的机制本质上是电影式的”。因为电影正是通过捕捉运动瞬间的静态照片来制造运动幻觉。这些瞬间从现实中抽离了所有流动性——毕竟瞬间只是运动的凝固图像,本质是静止不动的。柏格森认为,观众之所以能看到真实运动,唯一原因在于放映机带动胶片的前进运动。
3.2 时间的空间化
柏格森指出,正如电影试图通过连续的间断图像来创造运动幻觉,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同样通过数字进行度量——通常表现为观察钟表上等距排列的数字。这种认知方式使我们错误地将时间与运动视为空间形式,进而通过将其分割为静态固定点来进行虚假测量。
3.3 如何把握真实的“绵延”(Duration)
对柏格森而言,真实的绵延是持续继替、不可分割的。他将这种绵延比作一段旋律——音符相继涌现、彼此过渡。我们能在每个音符中感知其他音符的存在,却无法将其从旋律整体中剥离,否则整段旋律就会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音符视为连续而无间隔、渗透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唯有通过旋律整体的呈现才能理解,而非孤立的单个音符。柏格森最终得出结论:正如旋律,绵延处于永恒的运动、流变与生成之中,独立于空间且不可度量。
柏格森提出,要理解绵延,不能通过测量,而必须通过直接的体验来亲历它。唯有“置身于变化之中,才能同时把握变化本身及其连续状态”。为说明这一点,他以等待方糖在水中溶解为例:方糖从溶解开始到完全溶解所经历的绵延,与观察者等待溶解完成的个人绵延完全重合。此时,绵延不再是被思考的对象,而是被体验的存在。
4. 动画如何实现“生成”(Becomes)
在柏格森哲学中,生成是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流动状态,始终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中。对柏格森而言,生成正是这两个概念的汇合点,在此它们持续相互转化。
这种将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作为生成定义的观点,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的“存在论”密切相关。黑格尔认为:自我没有静态的存在,只有发展;没有永恒不变的“是”,只有持续的生成与矛盾。
这种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运动,可与电影运动机制相类比:银幕呈现的运动本身即蕴含着当下与过往、显现与消逝的辩证关系。
但是,动画中的瞬间不可能像电影那样具有即时性,因为动画影像主要并非通过对真实时间的分割与空间化来生成。人们常假定摄影影像才是唯一具有指涉性(指摄影摄像的光学-化学过程,胶片直接记录物理世界的光影痕迹)的图像,而动画影像(动画的影像生成不依赖物理实存对象,而是通过人工创造)则不具备这种特性——这一论点常被用来区分动画与实拍电影。
笔者希望探讨的是:动画诞生于间断性之中,却被我们感知为连续的。这种感知与现实的反差,使得动画成为探讨时间与生成哲学命题的绝佳场域。
本章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瞬间性生成、物质载体生成与银幕生成——论证动画如何自成一种生成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仍与柏格森关于绵延的原始结论遥相呼应。
4.1 瞬间性生成
在胶片电影中,运动的生产依赖于离散的连续图像,差异在这些图像间逐次发生。这些图像通过放映机运转,短暂定格于片窗之中。电影运动正是建立在影像的显现与消失之上,只不过这种消失因速度过快而逃逸于人类视觉感知之外。关于这种间隙不被察觉的现象,存在多种理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两种是“视觉暂留说”与“似动现象”。
这种显现与消失、在场与缺席的对立两极相互渗透,在银幕上创造出连续的影像流。观众通过画框序列感知到的即时现实虽然呈现为一种“在场”,但每一画框的消失又同时昭示着“缺席”。每一画框都被间隙抹除,而每一间隙又随即被新的画框所取代。因此,电影的本质正是显现与隐匿、在场与缺席之间的永恒流变——二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这种对立面的相互关联与依存,既呼应了黑格尔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同时性的思想,也令人想起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观点——他将生与死视为彼此嵌套、相互依存的存在。德里达认为,在放映机快门的开合运作中,影像缺席的间隙暴露出死亡,而随后影像的在场又将其抹除,这便是生命的显现。
动画将这一理念推向更深处,它通过赋予无生命物体以运动来实现“活化”,无论这种无生命物是绘画、木偶还是数字模拟。因此,艾伦·乔洛登科将动画理解为“既是动画与非动画的同时存在,又二者皆非”,并援引德里达的理论,称动画为“生死艺术”(the art of "lifedeath")。动画中的生与死具有本质关联:必须有死亡(单帧影像的缺席),生命(整体影像的在场)才能涌现,反之亦然。这种对立更体现在动画的本质中——通过运动使无生命体获得生命。这种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持续转化,正依赖于逐帧之间的差异。
这些差异—即帧与帧之间发生的变化—是银幕运动得以呈现的必要条件。如诺曼·麦克拉伦等动画师认为,帧与帧之间的差异比单独观看的静态画面更为重要。这种差异的幅度可以极为显著,如闪烁影片(flicker films)中所见,也可能微小到并置静帧时几乎难以察觉。连续图像看似完全相同,实则绝非真正一致——这正印证了柏格森的观点:无论事物显得多么静止,实际总在发生细微变化。
从技术层面看,这恰是对生命与时间感知的镜像呈现:连续性需要通过间断性来实现。瞬间既体现了柏格森与黑格尔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思想,也承载着德里达的生与死概念——这对立双方通过差异相互转化,由此构成了“生成”这一核心理念。
这种差异与间歇的重要性在诺曼·麦克拉伦的实验短片《线与色》中得到了极致展现。该作品通过刻意留白画格的方式,探讨了“间歇动画与痉挛式影像的可能性”,构建起观看体验的辨证运动:时而呈现连续运动的画格序列,时而展现彼此毫无关联的断裂图像。这种有意为之的创作策略,让动画作品始终游移于可见与不可见、显现与消失、流畅运动与闪烁定格之间。麦克拉伦通过画面间的差异性和胶片间歇性,不仅揭示了动画中“生成”的技术本质,更以运动本身展现了瞬间的动态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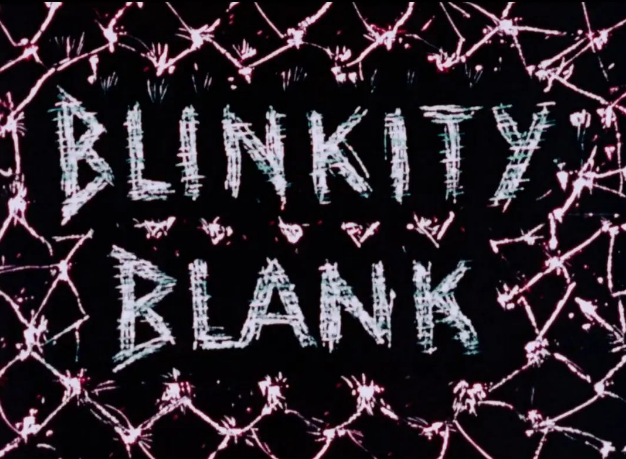
《线与色》
4.2 物质载体维度的生成
本节将探讨不同物质载体(直接胶片动画、定格动画与数字动画)对“生成”的呈现方式,并考察前文分析的胶片瞬间所承载的哲学意义,以及如何将其延续进当今的数字瞬间之中。
4.2.1 直接胶片动画
实拍电影的指涉性的核心在于:所呈现的运动曾真实被记录。这构成了运动双重时间的对立——动作发生的“过去时”与观众感知的“现在时”。动画异于实拍影像:动画是从尚未实体化的躯体中创造并提取运动。(注释:“尚未实体化的躯体”指“运动载体在被赋予运动前的存在状态”例如,没有赋予动作的定格偶,亦或是没有赋予动作的三维模型等,“创造并提取运动”指“动画师通过人工干预,而非物理记录,使虚拟载体产生运动”)。
以雷恩·莱于1966年去世前数月创作的《太空中的粒子》为例,该片堪称动画师运动内化于画面的典范。银幕上的线条是莱身体动势的转译——他将线条直接在胶片上的动作痕迹。然而这些线条又完全脱离莱的原始运动轨迹自由舞动,演化为独立的“生命显现”,莱影片中游走的线条绝非静止图像,而是充满生命力与能量的存在。
因此,动画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空间化、时间化的机械分割。与实拍电影瞬间定格的特性不同,动画图像本身就被铭刻着独特的绵延——它通过绘制过程的持续时长逐渐“成为”影像,记录着动画师的运动轨迹。而将这些图像组合成连贯运动的创作过程,则构成另一重“生成”:动画师在无法预知最终运动效果的前提下逐帧构建,恰如柏格森所言“未来不可预测”的哲学命题——万物皆处于永恒流变之中。
4.2.2 定格动画
定格动画以其独特的创作过程,最为贴切地呈现了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非存在到存在的生成本质。这种艺术形式主要通过操控既有的静态物体,通过逐帧运动赋予其生命力,因而成为通过帧间间隔展现特殊生成形式的典范。在摄影机前逐帧替换或移动物体的过程中,正是这些间隔使静止的“死物”获得了动态的“生命”。
保罗·布什2004年的作品《当达尔文沉睡时》完美诠释了这种替换动画的哲学。影片中,布什通过连续替换3000多只形态差异微小的死亡昆虫标本,使这些无生命、静止的“尸体”在运动中“复活”。这些昆虫在物种、形态与色彩间不断转化,其“生命”完全依托于帧间缝隙的差异而存在。正如布什所言:“单帧画面是探索时间的绝妙工具”——他的探索最终达成了一种变形效应,让进化过程直接在观众眼前展开,而这种进化完全通过差异来实现。

《当达尔文沉睡时》
4.2.3 数字影像中的存在与非存在
前文关于“瞬间”的讨论及柏格森对电影的思考,均基于胶片与放映机的技术语境。这些思想如何延伸至数字影像领域?
笔者想要着重探讨数字影像与胶片影像的差异,不在于图像的生成方式,而在于二者在银幕上创造运动的运作机制差异。因此,本文关注的不是影像作为媒介的存在模式,而是其在银幕上的生成方式。
在胶片影像中,技术过程体现为胶片上连续瞬间的快速排列;而在数字影像中,屏幕处于逐行扫描的持续过程。为稳定图像,每个“瞬间”实际由两个“半瞬间”构成——前半帧与后半帧的交错。这种机制与扫描线运动结合,在数字屏幕上形成恒定图像的幻觉。两个半瞬间的咬合使观众无法察觉帧间仍存在的闪烁。
尽管数字影像与胶片影像同样依赖间断的连续瞬间,关键区别在于:数字影像的每个瞬间都是不完整的。扫描线在屏幕上的交错运动,使两个半图像之间形成完整画面,并沿屏幕移动——持续让位于下一个半图像的出现与消失。这意味着数字影像作为整体从未完全在场,他通过技术流程不断自我补完,却又因始终只呈现半帧而永远无法完整显现。
尽管数字影像通过非连续的扫描流与咬合半图像否定了胶片电影的线性间断图像流,但它仍能通过不同的技术路径,呈现与柏格森“绵延”和“生成”理论相似的核心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种与此理念尤为相关的动画技术应运而生——程序动画(procedural animation)。尼基塔·迪亚库尔使用Cinema 4D动力学系统创作的《丑陋》即是一例。迪亚库尔并未以传统方式绘制动画,而是创造了链接虚拟提线的木偶系统。最终生成的动画并非源于创作者在时空维度上的直接控制——他既未绘制中间帧,也未预设具体动作,而是设计了一套允许随机性的条件系统,让木偶“自主”生成动画。这种创作存在于“控制与随机之间的暧昧地带”,其本质是与传统逐帧动画相悖的过程动画——角色在系统中自行展开与生成。迪亚库尔赋予角色物理躯体,但其状态因环境参数持续变异,连创作者亦无法预知其具体运动轨迹,仅能设定基本行为方向。

《丑陋》
4.3 银幕生成
当我们超越技术过程的维度来思考“生成”时,动画中呈现的形象本身运动便成为新的探讨焦点。
索尔维格·冯·克莱斯特1992年的短片《万物流变》深刻诠释了运动在动画中的核心地位。该作品基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万物如河流般流动”的著名比喻,全片从未出现静止画面,而是通过三重交织的运动实现:
a.摄影机的连续运动——一镜到底
b.画面内人物与事件的运动——常与摄影机运动形成对抗性张力
c.人物与物体的形态互变——变形动画实现场景间的无缝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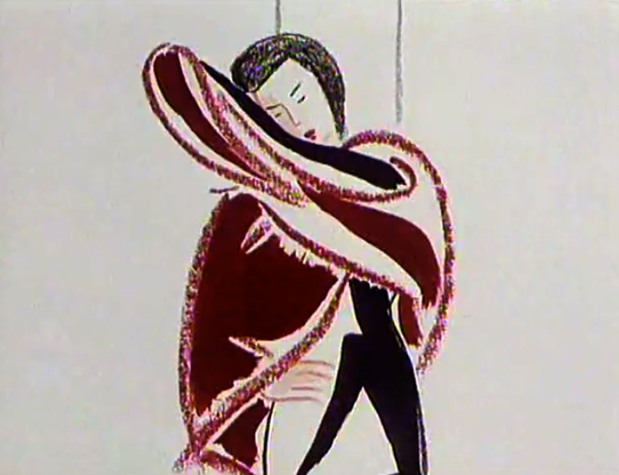
《万物流变》
正如冯·克莱斯特所言:“没有画面是固定的,没有事物维持原貌,这是一场永恒的变形”。这种持续蜕变完美体现了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皆处于永恒流变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和柏格森相似,赫拉克利特将“生成”视为“存在与非存在”交织的过程,唯有通过运动与变化,才得以“生成”——而动画正是这一哲学思想最直观的视觉呈现。
动画(anim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anima(气、呼吸、灵魂、精神、心智)。回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中关于灵魂运动的论述,他认为:“运动最贴近灵魂的本质,万物皆被灵魂驱动,唯灵魂能自我驱动。”这意味着灵魂的特性在于其运动不假外求,而是源于自身。
这一思想揭示了动画运动中耐人寻味的双重性:无论是直接动画、定格动画还是数字动画,其影像皆为创造之物——每一帧的诞生都依存于动画师的运动。动画影像之所以运动,是因为“运动通过运动载体的物质性被赋予”。银幕上的运动虽看似独立于创作者之手而即时呈现,实则永远归属于某个过去的运动时刻。
但是,尽管动画的运动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我驱动”(因其运动源自动画师的创造),但动画却呈现出了自主运动的表象。动画最本质的内核在于将无生命之物转化为有生命之态,而非对既有运动的复制。动画影像通过专属自身的运动(指动画师的创作行为)获得存在,但这种创作运动与银幕上呈现的运动并无直接关联——它并非对动画师动作的摹写。
这引出了一个与澳大利亚哲学家杰夫·马尔帕斯不谋而合的结论:动画影像的运动归属于动画影像本身,其真实性不亚于实拍影像的运动。由此笔者认为,动画绝非简单的运动幻觉,由于运动在银幕上的即时呈现与拟自主性,动画影像的运动与实拍电影同样真实——动画确实是图像自身在运动,这种运动内在于图像本身而非图像被外力移动。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图像本身被赋予了生命。
综上所述,动画运动的核心特质在于其与起源的彻底脱钩。这种独立性使得运动能够完全自主地演化,实现形态间的任意转换。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将这种绝对自由的变形特质称为“原生质性”(plasmaticness)——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一种通过绘图呈现的存在,它虽已获得确定形态,却仍像原始原生质般行为:尚未拥有“稳定”形式,能幻化为任何形态;它跃动着跳过进化阶梯的横档,将自己附着于动物存在的所有可能形式之中。
爱森斯坦的“原生质性”理论在平冈正展2015年的作品《在暴风眼中》得到了完美诠释,正如片名所示,平冈创造出一部永续旋转、螺旋运动的动画,刻意玩弄重力与透视法则,让几何形态持续变形。通过这种流体般和谐的运动效果,每个动作与图像都处于未完成状态——不断自我构建、解构与演化。他的画帧始终处于“生成某物图像”的过程中,当观众即将辨识出形状的瞬间,一切又再度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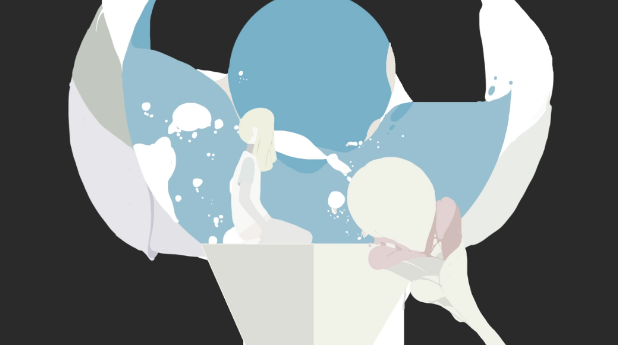
《在暴风眼中》
平冈笔下永续延伸的线条礼赞着变形(metamorphose)的理念与爱森斯坦的“原生质性”,其流动性将观众卷入迷人的运动之流。这种效果使爱森斯坦断言:“动画不仅是赋予生命的艺术,更能”唤醒观者的生命感,让其体验自身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凭借其无尽的运动、转换与变形能力,动画成为“对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的庆典,摆脱意义生产与责任重负”。正如爱森斯坦所坚信的,动画凭借其“原生质”特性,成为充满意外与变化的进程。
5. 结论:动画作为哲学的映射
柏格森认为现实本质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continuity),我们却将其感知为断裂;而动画正构成其镜像——它以断裂的瞬间为现实基础,却被我们感知为连续。笔者认为,若将注意力转向动画直接呈现的运动本身,而非拘泥于其时空分割的索引性价值,动画恰能精准诠释:1.自我与世界的感知的关系;2.柏格森“生成”论的多维呈现。动画由此成为“存在”的哲学镜鉴——通过其特有的运动诗学,折射出我们认知机制中连续与断裂的辩证交响。
作为观众,我们目睹动画形态在眼前生成——它们的运动徐徐展开,存在逐渐显现,并持续经历变化的过程。正如爱森斯坦所言,动画让观众得以体验生命最核心的持续变化形态,亲眼见证变化的发生。正是通过观看运动、并被运动裹挟前行的体验,我们才得以感知自身流动的存在状态——我们不仅体验着动画的绵延,也直接体验着个人生命的绵延。观看动画的生成过程,让我们通过置身其中,直接触摸到真实绵延的片段。
对赫拉克利特而言,宇宙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万物皆依赖其对立面以实现生成。动画通过呈现时间流中诸多对立面的统一,完美映射这一思想。正是在存在与非存在、稳定与不稳定、过去与现在、显现与消逝、生与死、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流动中,动画使我们理解生成的真谛。
正如德勒兹阐释柏格森思想时所言:“生成既非某人的生成,亦非某物的生成,而是发生于事物之间的运动。”过去状态与未来状态之间的差异促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生成。麦克拉伦对动画的定义亦印证此理——动画的本质在于“帧与帧之间发生的差异”。
柏格森认为过去持续保存于当下,每一刻都同时涵容部分过去与未来,从而形成不可分割的时间之流。
通过动画中画格的连续更迭,每一帧都是此前不存在的躯体的诞生,同时也导向其消亡——随即在下一帧中获得重生。动画中的每个当下瞬间倏忽涌现又转瞬消逝,指向未来帧中的生成。动画正是将人类的存在本质—一种纯碎的运动形式,处于永恒的生成之中—转化为银幕上运动之在场的艺术媒介。
动画通过三个维度不断“生成”:1.技术维度——通过瞬间与图像的涌现呈现连续性;2.物质维度——生产蕴含绵延的图像载体;3.运动本体维度——在银幕上展现无限的变形与转化。
动画以“不断流变、始终面临重新界定与重构”的形态,印证了柏格森“任何形式都只是过渡的瞬时快照”的论断。对柏格森而言,生成是世界持续显现的过程,它通过变化、对立与差异解释万物(包括我们的身份)的构成。如果说动画是“之间”的艺术与差异的艺术,那么它本质上更是生成的可视化艺术,让我们得以体验真实的绵延。
最终,笔者认为动画能够提出关于存在本质、我们在时间连续体中的位置以及绵延感知的本体论与现象学追问。动画通过多种方式展现过去与当下的对立统一,例如,胶片齿孔的流转;动画师过去动作与动画当下显现;瞬间闪烁的时序叠加等等。
动画的真正主体是运动与时间本身,而非其表象再现。当它挣脱幻象的桎梏时,便获得了关乎其自身与我们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它在呈现生成的同时,自身也在生成。
动画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存在者,但这些存在者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恰如我们自身),他们通过流变获得存在,并持续在流变中生存——存在于生成在此合而为一。
作为一种媒介,动画能以多种方式探讨生成;与此同时,媒介本身也在持续成长与蜕变,不断拓展动画的可能性边界。随着技术与方法的演进,动画作为艺术形式将持续发展。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认为:真正的活媒介,永远处于自我转化的状态。
因此,在内容、物质载体与机械原理之外,动画媒介本身也处于永恒的生成状态:它不断质疑自身身份,实验自身物质性——就像我们的存在状态一样,它持续自我更新,其未来永未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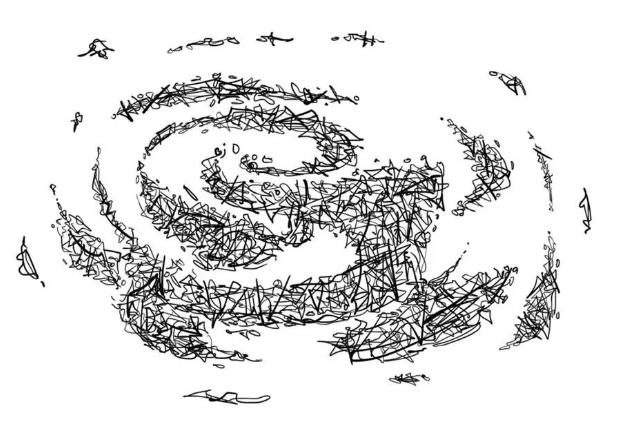
《河流》(作者自绘)
原文链接:https://www.asifa.cn/info-31-c.html

ASIFA Academic Magazine致力于动画领域的深度学术研究,面向全球动画学者开放,欢迎大家投稿。
读者如想获取刊物,请联系ASIFA-CHINA国际动画协会中国分会。
咨询电话:010-62662716
投稿邮箱:works@asifa.cn; contact@asifa.cn。

